党刊朗读丨曲中闻折柳·乡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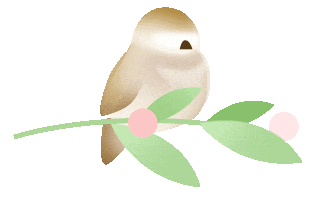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种乡音都藏着一个故乡,一群人,或者一份回忆。十里不同音,老家声音带着烟火气在空气中激荡。除了阴雨天,每天第一个“歌唱家”是公鸡,从三更打到五更,人们按鸡叫节奏起床:倒尿盆、打扫院子、下地、挑水、做饭,拉风箱声成了清晨协奏曲。
早饭时或半头晌,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:卖果子的、敲梆子卖豆腐的、磨菜刀的、收鸡蛋的、敲波楞鼓卖糖果百货的,春天还有卖小毛鸡、小鸭的。
中午村子稍静,下地干活的劳力回家吃午饭,饭后躺在炕上打个盹或睡个晌觉。过半晌阳光不太晒了,再扛起锄头拿着镰刀下地干活。傍晚村子又沸腾起来:劳力牵牛赶羊回家,车把式甩响鞭子,河湾里的鹅鸭摇摆着呱呱归窝。
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声音最浑厚尖细的是河沟蛤蟆和树上知了。春风融冰后,蛤蟆第一声“呱呱”叫,老话说“听到蛤蟆打呱呱,再有六十天吃古扎”,预示着俩月后收麦吃面。
老家管未脱壳的知了叫爬爬,成虫叫老哨。村边杨柳多,傍晚全家拿手电找爬爬,最多能抓小半盆,撒盐腌着防脱壳,第二天油炸便是美餐。爬爬高蛋白还能当药材,捡爬爬皮能卖钱换笔记本铅笔。知了从夏叫到秋,开始吵得人睡不着晌觉,听惯了倒不觉得是噪音。
我们这代人经历丰富:交过公粮、骑过二八大杠、看过黑白电视、听过磁带录音机、点过煤油灯、看过露天电影、画过假手表、吃过伍分钱冰棍儿、听过小喇叭。
农村物质虽匮乏,精神生活却多样。家家墙上挂小喇叭,早晚播新闻音乐,公社常插播通知,后来电线杆装了大喇叭,村支书操控播放音乐或通知。家境好的买“戏匣子”(收音机),傍晚人们守着听刘兰芳说评书,没听上的要么等重播,要么找听过的人复述。
晚上看电影是大事,不管刮风下雨、路途远近,跟着放映队各村追着看。《甜蜜的事业》启蒙了农村青年恋爱观念,让谈恋爱不再难为情。有黑白电视的家庭,全村人围着看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,剧情至今历历在目。
老家声音带着节日色彩,过年时最丰富。春节前后爆竹声声,硝烟裹着年味弥漫。初五六后,村里召集男青年踩高跷、组鼓子秧歌队,元宵节到邻村巡演,男女老少闻声看“闹玩艺”,这习俗延续多年。
我当兵前年年参加踩高跷,巡演时家里大人跟着帮忙化妆解绳,这手艺让我当兵后还能在高跷秧歌队表演,很多战友只能当看客。春节和元宵还有戏台或收音机里的样板戏、评剧、吕剧,老家有种类似吕剧柳腔的勾梆戏,小时候爱听老人们唱《小姑贤》,如今已听不到了。
作者:刘学农
主播:孙昕唱

 微信
微信
 手机版
手机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