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刊朗读丨曲中闻折柳·乡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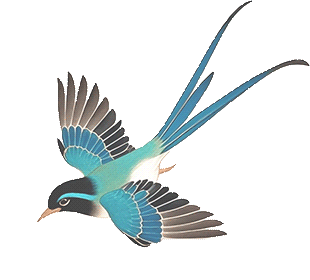
土地的仁慈、河流的博爱、谷物的恩泽、岁月的爱抚,让家乡成了游子的精神之母。提及老家,儿时影像便在眼前重现。老家春夏秋冬和黄河下游景象相似,却有独特的地理环境。
村里两个生产队三四百口人,集中住在防洪涝垒筑的村台上。平原高台必有洼地,村前大水湾如今已基本淤平。人口增长后,村台容不下,有人便在周边盖房。
儿时,远望村庄,满眼是原始的土黄色:土房、土墙、土院、土路,刮风时黄土满天飞。春天主打白色:盐碱地化冻后泛着白碱,刮掉浮碱种上耐碱棉花,出苗前盖着白色塑料薄膜;杨柳泛绿,槐花、榆钱雪白,狗尾巴草(老家叫茅草)吐着白绒,地黄(老家叫青稞子)顶着红白相间的花。
春入夏,颜色由浅变深:黑油油的小麦,深绿的杨、柳、槐、枣叶,贴地生长的地瓜叶、瓜藤,白色地瓜花、喇叭花格外显眼。割完金黄小麦,绿色玉米秆呼呼拔节,不到两月就比人高。
夏日乡村景色丰富,除了绿植,村前大水湾是一景。大雨后水湾蓄满水,中午傍晚成了大家的集结地:男孩戏水摸鱼,父母在湾边大树下扒红麻杆皮做麻绳;妇女在湾边用木棒捶打洗衣,傍晚成了女人专属区域。
立秋后天气转凉,早晚下地要穿秋衣秋裤,田边拔猪草会被露水打湿裤腿。干活先凉后热,出汗后凉下来更觉轻松。一年两大收获季:“麦秋”时间短、强度大,家家把攒的咸鸡蛋、腊肉拿出来给劳力补体力,“忙饭的”(老家对老婆媳妇的称呼)多舍不得吃;秋收秋种近两个月,是“长尾巴秋”。收玉米要从水洼里把棒子装袋扛到地头,掰棒槌、扒棒皮、晒棒子,家家房顶、庭院满是金黄玉米。
棉花开了,晌午头人们腰扎布兜拾棉花,头几茬白棉价高,霜降后棉花发红价跌。那时棉花是家庭主要收入,供孩子上学、盖房、娶媳妇,现在老家已很少种棉花。
收完玉米便推粪撒肥耕地种麦,犁耙耧全派上用场。分田到户初期,没牛耕地就靠锨翻,我和老爹推着独轮车送粪,撒匀后翻地、荡平、掘沟、撒种、蹚平踩实,常借着月光或清晨微光干活,盼着快点干完休息。
种完小麦已到深秋初冬,早晨下地要穿薄棉袄,整个秋收秋种下来只剩一个“累”字。冬天是农闲时,没打工做买卖的说法,人们依偎北墙根或玉米秸垛晒太阳。冬日褪去绿装,满眼土黄,偶有白雪盖在房顶或麦苗上。
作者:刘学农
主播:孙昕唱

 微信
微信
 手机版
手机版